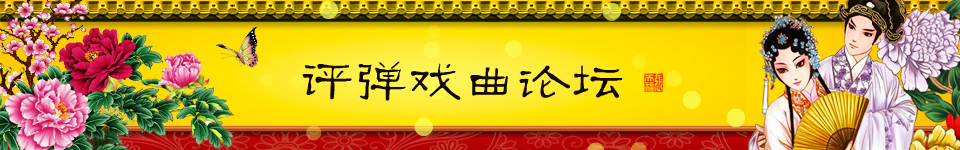二、推测“涯词”即“词话”0 a3 t3 }* P1 Y0 `5 e
, w, r5 a! G: Q6 P
从上可以获知:“陶真”唱说很杂,有鼓词、琵琶词、渔鼓、道情、莲花落…;既有“小唱”形式的赵五娘《琵琶词》,又有“说话”类的《雷峰塔》。《雷峰塔》既是“陶真”,又是“词话”,这从成化《说唱词话十六种》中的“《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》,全书九百多句,则均为七字句”,也可以知道“词话”也有“只唱不说”的。更多时候,“词话”则指“有韵有散”的“说唱词话”,实物有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 明成化年间(1645-1687) 刊刻的《说唱词话十六种》(下简 成化唱本):
, u" I5 G) M6 P) u( x6 {8 f4 |, y第一册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阅索出身传(等四重)
& z& B! b9 c* C: w第二册 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& B# o2 b4 L( n2 |+ O
第三册 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
6 x/ b; f, R+ ^4 S% Z. C' y第四册 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(等三重)0 a7 e" ^: Z) {5 O
第五册 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
/ P3 `( m: [* t% h- [. W第六册 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1 d3 Z/ _1 X6 K7 I+ t
第七册 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7 [# ]! X, h, a- D, {
第八册 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/ V' |. x, X( g9 C2 |" P
第九册 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兀十五夜看灯传+ D7 l5 C7 p4 D
第十册 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
8 p {, c9 y) x, n, R2 e1 k6 }第十一册 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
' i! n3 ]9 ?7 r$ s3 B第十二册 新编刘知还还乡白兔记
@) `/ N) i8 q& }影印全12册,(末册为南戏《白兔记》早期刊本,不是“词话”)。版本特点是粗黑口,说、唱、赞等字样都用墨围,文本主要是二、二、三的七字句,间有“攒十字”,有说有唱。《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》,全书九百多句,则均为七字句。《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》、《新刊全相说唱石郎驸马传》,封面题目双行中夹“全相说唱词话”、“说唱词话传”字样。今总题《说唱词话十六种》即由此来。 ^! o2 y" m/ L3 u. E0 T3 F8 q, M
+ V C; x4 Y% W$ f. e. U- u
“陶真”中,故事人物说的话,全用“诗赞”,口气全无;“说唱词话”中, 故事人物说话虽仍和人称“绑定”,如“xx说道:…”,但毕竟用“平话”,便有了“亲真”的意味,可以为“偶戏、影词、傩戏”这样有人物形象出示的哑剧配音。) m3 |; r" h& i# G4 o
; W( u# `' q! e1 ]. O贵池傩戏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性戏曲,至今仍活跃在安徽贵池、九华一带,其所据本和成化唱本“语词完全相同或极为相似”,因而通过田野考察,可以获知这批成化唱本更多细节和许多纸面外的东西。这儿也仅就其“搬唱”形式,推测“涯词”即“词话”作一论述。
( \. L- E9 A+ j. u, f! j- k8 L, P关于“涯词”(一作 崖词), 西湖老人《繁胜录》:“唱涯词只引子弟,听陶真尽是村人。”《都城纪胜》中说:“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,铁骑公案之类,其话本或如杂剧,或如崖词。”
9 v- ]7 o/ {. a# d: C" Q前一条说“涯词”是和“陶真”一样的讲唱伎艺,只是受众为“子弟”;后一条说“傀儡”(偶)戏所据演本,有象杂剧一样为“代言体”的,也有象“崖词”一样为“讲唱体”的。李雪梅《元代说唱词话研究》(http://www.doc88.com/p-4921544842165.html):! q4 F C, I2 N
(贵池傩戏)演员上场进行的是哑剧性表演,真正表演说唱的是后台或台侧的两位先生,其所持唱本有一个“总稿”剧本,…这些剧本不是我们理解的“代言体”,而是第三人称的说唱词话体,王兆乾将这一形式定义为“肉傀儡”。 ~6 L7 b6 Y: v e
5 l1 q' k1 K8 j% I1 X' P
这种“第三人称的说唱词话体”意即“崖词”。元史料中有“演唱词话、自搬词传、般说词话、搬唱词话”数说,一般认为“般”、“搬”同义,即今“扮”。从傩戏看,“般”、“搬”也许有不同的意思,“般唱”为代言体,“搬唱”为讲唱体。
2 i+ b9 e9 k( u0 ~! c7 ^
* B2 }0 L1 s# H5 I0 _& V( W. |) e0 y按讲唱弹词是“旁述体”,但后来也有把“起角色”的弹词称为“代言体弹词”(实为 表白混杂体,简称表混体(日 轮田直子 定名),下仍称 代言体)。但毕竟和戏曲的“代言体”不同,“代言体弹词”中“故事人物说的话”是借“说书人的口”说出的,是一种转述、带话、代宣、学舌…,即不是一种亲真行为;而“代言体戏曲”中“角色的白”是由角色“亲口”说出的,所以我把“代言体弹词”中“故事人物说的话”,降一层定义为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。类之,“唱说滩簧”中,也有“第三人称的代言”。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和“第三人称的代言”是“旁述”和“代言”的中间体。2 V" o# z8 ~% X" f) H. L
堪作“旁述体”(不起角色)样本的《陶真•雷峰塔》中有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:
5 l% w6 |5 _9 r- o1 V$ U! i你听白娘说事因:奴家为你来到此,路途辛苦好难行,到此就把新房赁,特来请你到此临。当初曾把终身许,奴家性烈不更人,今朝既得重相会,愿做同床共枕人。
% a, s+ C1 [2 o' n1 y
+ Q9 z2 ?7 J+ g9 S- Q2 M, [和“起角色”的“代言体弹词”《南词•白蛇传》中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:
$ Q( H0 @$ Y, v5 h《西江月》只为西湖游玩,独自一身淘情。叫船避雨遇佳人,惹起风波不定……(引)小生姓许名仙,浙江钱塘县人氏,年方十八。只因父母早亡,尚未联姻……(唱)那时许仙即忙来打扮,要到西湖走一巡。
' W, Q9 w$ c; O" N的区别是:“起角色”后,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会偏代言,同时七字句趋向说散,更接近口语;未“起角色”前则偏旁述,如“奴家为你来到此…”,平语收缩“均”为七字唱。9 `' Z& l! x: d# A7 z! ^
“第三人称的代言”反是,例不赘。: B$ P k, N9 m# b( _% W* J9 k3 B0 x V
2 ~1 }8 ?: d" O1 Q" X
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和“第三人称的代言”属性的偏摆,是讲唱和戏曲可以转换的一个“机理”,越是草台幼本,这个特点就越明显。在代言体戏曲中找到“诗赞词”,如叶德均统计《元曲选》100种杂剧中,有92种有“诗赞词”,占90%以上;旁述性的讲唱弹词刊本中且标(生)、(旦),都可用这个“机理”得到解释。因而也并非有真正的“旁述性戏曲”或“代言体弹词”存在。$ k0 d' t& `/ c4 u8 A
1 @- L+ ]7 b M( h
傀儡偶戏(包括傩戏、影戏)都有一个“妆定”的道具或假面“角色”,但这个“角色”无法开口,需说唱人在旁侧“代宣”转述 ,因而其话本“或如杂剧,或如崖词”,指是兼可采用“戏曲”或“讲唱”的形式。“陶真”是偏旁述的“讲唱”,“词话”是偏代言的“讲唱”, 傀儡话本之“如崖词”,则必谓“讲唱词话”而言,因其讲唱而偏“代言”也。“崖词”即“词话”,由傩戏用“第三人称的说唱词话体”可征。 |

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QQ空间
QQ空间 人人网
人人网 腾讯微博
腾讯微博 Facebook
Facebook Google+
Google+ Plurk
Plurk Twitter
Twitter Line
L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