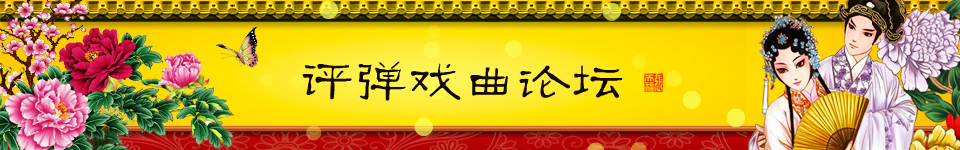我与评弹艺术 吴宗锡 口述 王其康 整理 2017-04-06/ L% Y- n# g/ [" \' i
吴宗锡,祖籍苏州,1925年3月出生于上海。诗人,作家,戏曲曲艺理论家。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获得者。曾任上海评弹团团长,中国曲协副主席,上海市曲协主席,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,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组长。, b" R+ _, T( H
接受任务 开拓起步- N5 g* W7 r- s" D( x: s- H
在学校毕业前,我已开始文艺创作了。1945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后,一直还是搞文艺的(这个文艺是指新文艺工作)。1948年冬天,地下党联系人约我到现在的静安公园,当时的外国人公墓。我们边走边谈,他提出了领导上要我去搞戏曲的决定,我当时认为戏曲不是进步文艺,是看不起戏曲的,心里很不愿意。但这是党的决定,应该服从,只好接受。后来就由刘厚生同志来联系了,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,搞上海地区的戏曲。谈分工了,我想,自己祖籍为苏州,苏州的评弹文学性高一些,也较高雅一些,就主动提出说,我来搞评弹吧。其他同志就分工搞沪剧、滑稽等。
4 f# z/ z: X% r( Q/ F' W3 e 于是,我就开始搞评弹了。我开始跑书场收集资料,对评弹小报、“书场阵容表”,乃至根据评弹书目改写的绣像小说、连环画等进行调查研究。没有办法去接触评弹艺人,我就想通过一位评弹小报的作者去接触评弹艺人,这是开拓工作的起步。, }$ v; n& U. s( L
我接触评弹艺人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,1949年5月28日。刘厚生同志通知我28日上午到泥城桥民营的大中华大陆电台去,那里有我们组织的特别节目,要我代表组织去联系艺人。电台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人配合的,特别节目除了由主持人宣传党的政策,安定人心外,也要评弹艺人唱一点我们带去的宣传材料。我那时不熟悉评弹开篇,把我写的唱词交给他们唱,第一个碰到的是赵稼秋,问他这你们能唱吗?赵稼秋是擅唱白话开篇的,他连说,好唱好唱。把唱词都接过去,练了一下,结果都唱了。那天来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艺人,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接触。
; z2 S& f2 E z4 g5 l' r1 x+ n9 b; r 接着党组织叫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报到,分配到军管会文艺处工作,联系苏南剧种,评弹也还是归我联系。
: S6 V1 N, c7 I% P/ z, U 当时,根据“改人改制改戏”的戏改政策,到评弹界去做工作,联系评弹艺人。我们主要用地下时做群众工作的方法,和群众交朋友,找骨干,组织他们学习,推动他们说新书。最近听金声伯讲起,那时他十七岁,坐在协会门口喝茶,看见一位工会干部领了我走进协会去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到寿宁路的老评弹协会。- p. K7 |0 ~7 l) k& A3 R
在协会里我普遍接触艺人,而偏重于较年轻的,如周云瑞、张文倩等,还有是正派和愿意靠近我们的人,从中物色可以作为骨干的人,这样,潘伯英成了积极分子。同时还组织会员学习,有妇女组,青年组等。妇女组在沧洲书场,组长徐雪月。潘伯英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汇泉楼,用上午时间,每周一次,学习材料是“工人读本”,从劳动创造世界学起。有些响档上午不出来的,潘伯英告诉我,在南京路成都路有个“大观园商场”,里面有个茶室,他们每礼拜一天,在那里唱京戏。你那辰光去,就能碰到他们。于是,我就在这辰光去了。也不打扰他们,等他们唱好京戏,就请他们坐下来学习,逐渐成了常规。& a( I) h b6 F
那时候,认为评弹说的都是封建的内容,要推动他们说新的内容。但是评弹艺人很多,一人或一档(两三人),说一部书都要换新内容,困难很大。潘伯英向我建议,组织大家演书戏,内容为潘伯英改编的《小二黑结婚》,在南京大戏院(后改为上海音乐厅)作为劳军演出。由协会出面,当时在上海有知名度的艺人都参加了。蒋月泉演小二黑,范雪君演小芹,刘天韵、张鉴庭、张鸿声、朱耀祥等都参加了,周云瑞、张鉴国等组织乐队伴奏,这样等于在上海的响档全亮了相,表示拥护共产党,愿意说新书了。
) Q1 j- t0 r2 h5 d) ]* ]0 B 原来评弹的老协会遵照领导指示,要进行改建。于是我和潘伯英等商量,帮助他们进行改选改建。改建大会是在军管会文艺处的大礼堂举行的,改建后称评弹改进协会。后来便是在改进协会的基础上,建立了中国曲艺协会的上海分会,后又改称上海曲协,也都是我主持筹建的。这也可说是开拓工作。 g u' l% F- Z! w* Q) M3 N
进入评弹团3 J X& ~4 d; M: P
1950年,军管会文艺处转为上海市文化局,我便在文化局戏改处编审科当副科长,并兼任《大众戏曲》副主编(主编梅朵),和评弹的联系少了。
# p, Q U2 }& {% ` 1951年,知识分子思想改造,我被调到文联当治淮宣传工作队副队长。1951年11月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(今上海评弹团)成立,第二天整团调来参加治淮,说也凑巧,便又归我领导。
) E: J3 m$ V. b$ N2 c- y8 R 我们先后到漴潼河和佛子岺水库工地,与民工、工人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。不但我们都受到了教育,得到了锻炼,我和评弹团的艺人们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了。& J0 b4 L0 i3 g+ ~& i( `, b
原来文化局派的一位驻团干部是兼职的,他没有参加治淮,评弹团回沪之后他也无暇兼顾团的工作,局里商量要派驻团干部,我觉得坐机关不如基层剧团活络。一天,刘厚生同志谈起派人驻团的事,我就说,我去吧。领导同意了。我就去了评弹团。这样我就真正走进评弹了。那时,评弹是艺人当团长,正团长刘天韵,副团长唐耿良、蒋月泉,还有一位秘书张鸿声,兼演出股长。局里派来的干部叫党代表或政委太严肃,就叫教导员。还有一位搞创作的陈灵犀叫指导员。后来到1954年,决定艺人不当团长,我就当了团长。所以我不是评弹团的首任团长,但是干部当团长我是第一个,并得到了陈毅市长签名的任命书。
3 g4 e( ^8 X$ |6 \. r9 V3 m0 B6 @% A 我到评弹团去,局里就派我一个干部。我是自己去的,因为评弹团的演员都已和我熟悉,不需要介绍了。可是当时,我和他们之间的反差很大。我当时二十八岁,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当了干部;他们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,年纪大的已经四十多了,文化程度不高,但是社会经验丰富,从小学了说书,就在社会上接触各阶层的人物了。所以后来陈云同志说:“他们是五颜六色都见过,鉴貌辨色。吴团长啊,我替你想想,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。”我当时也有点糊里糊涂,不过,我当时作为党员干部,他们是尊重的。和他们一起参加治淮,也建立了初步的友谊。当然后来在工作中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和意见。再后来,我熟悉了他们,他们也熟悉了我,觉得我不带私心,是一心一意要和他们一起搞好评弹事业,办评弹团的。三十多年来,我们建立了感情,在艺术上,他们也对我有了信任和尊重。9 m# ?& _/ @2 S) {3 t9 v
不过,一开始,工作上的困难还是不小的。首先,评弹演出以档为主,评弹团是从来没有过的,评弹团该怎样办,从来没有一个样板,也没有地方好学。领导提出的办团宗旨是四个字“实验示范”,戏改政策是“改人改制改戏”。我们领会,要“实验”的就是对评弹艺人和书目的改造与改革。另外,我也参考当时一些文工团的办法。评弹艺人以“档”为主,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的,评弹演员每一个人或每一档有一部书,谁的听众多就是谁的艺术好,收入多,谁也不服帖谁。到了团里要评级评薪,那就矛盾大了。别的剧团有主要演员,可是在评弹团,大家都是主要演员。分“观摩票”不能谁有谁没有,安排演出,场子大小,档子前后,都会有意见。 |

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QQ空间
QQ空间 人人网
人人网 腾讯微博
腾讯微博 Facebook
Facebook Google+
Google+ Plurk
Plurk Twitter
Twitter Line
L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