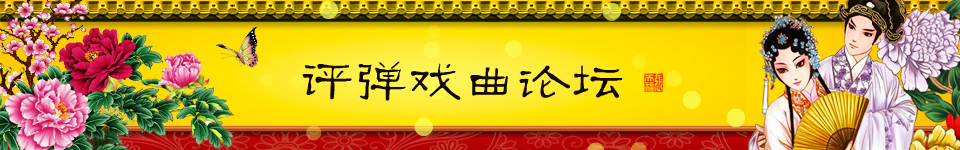结束语
# ]: k1 E9 _# A! }+ `* R* q4 a0 r1 ~8 ?7 E3 ^1 k
不知不觉,《苏州评话杂弹》系列接近尾声了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苏州评话又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,记得某位评话名家说过:要说好评话的话首先要耐得住寂寞。但是在这个浮躁的商业化社会里,谁又能耐得住寂寞呢?说书人变得很媚俗,听书人变得很浮躁。作为说书人,在现在,有些评话演员借着“评话”之名讲故事,他们侃上海大亨、说贪官、走私犯,热衷描绘暴力、血腥事件,早把优秀传统书目弃之脑后。这类“伪评话”,有评话之名,却无评话魅力,也就很难留住听客。又或者干脆跳槽而去,经商的经商,从事娱乐业的从事娱乐业,挡主持人的当主持人,是在是可发一叹。而作为听客,相当多人实际上都不是静下心来听书的,而是来猎奇的,因此,有所谓的现代书一出,很自然就引起了这部分人的兴趣,因此他们就将之捧的很高很高,但有没有新意呢,实际上都是在按官方的路子在走,了无新意。目前评弹界即是如此,会不会再出现如同“斩尾巴”运动那样的情况呢?这个就非笔者所能遇见的了。
5 S4 w, W4 p, B9 D* Q, Q" |/ p综上所述,苏州评话是苏南地区民间文化的一座宝库,它博大精深,笔者所见所闻仅仅是其冰山一角,因此以上见解不免就有贻笑大方之处,还恳请看官海涵!新年新气象,祝大家健康、愉快!(完) |

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QQ空间
QQ空间 人人网
人人网 腾讯微博
腾讯微博 Facebook
Facebook Google+
Google+ Plurk
Plurk Twitter
Twitter Line
Line